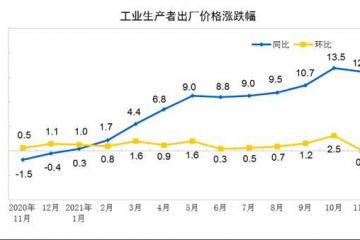小婆与我奶奶年龄相仿,却是残疾人,走路样子像螃蜞,一跩一跩的。因口角歪斜而口齿不清,吊嘴,一笑,口水直流。
因为残疾,干不得农活,无非是拣棉花,望鸡鸭,赶鸟。每当早晨,听到队长喊“小婶妈”,她知道有活干了,就吸溜溜喝了粥,一跩一跩往仓库场或田野里赶。叫她“小婶妈”“小婆”,因为她是鼻公的小老婆。鼻公的大老婆阿品,小脚、卷发,像美丽牌香烟上的女人,却不生育。于是阿品帮鼻公选了小老婆。阿品有心计,怕失宠,就选了家贫又残疾的阿彩,就是小婆。
不几年,新中国成立了,一夫一妻,鼻公选了阿品。阿彩就此与鼻公只合日头,不合灶头地住在一个屋檐下。每年阿彩的粮食、柴草还要由鼻公供着,那是他们离婚时,我爷爷定的。爷爷与鼻公是发小。他说:阿彩苦恼人,又残疾。你叫她去哪里?你要养她。鼻公唯唯。
从此,阿彩就住鼻公隔壁的厢房内,一间房一隔两,半房半灶。一扇贝壳的木窗,一只行灶。一烧,满屋子烟。
照理,她的一切有鼻公供养着,何须劳动。可阿彩说:只猪猡也上了岁数,还摊上我这个残疾,也苦恼。“只猪猡”是我们那里对自己男人的昵称。阿彩想减轻鼻公的负担。于是干赶鸟、看鸡鸭的活。一天下来,人家十个工分,阿彩才三个。阿彩不嫌,她要自食其力,有尊严。
那年头,田多、劳力少。手脚齐全的,无分老幼,都干体力活去了。赶鸟、看鸡鸭的事就阿彩一人揽着。她大多的时候腰间束条作裙,在仓库场上看鸡鸭时,我们往往在柴垛间玩翻筋斗、捉迷藏。她常将我们招呼过去,然后从作裙口袋里掏出炒蚕豆、白胡枣。她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有时念叨说,我的弟弟要是活着,比你们要大出许多,你们都该叫他叔叔。
曾听奶奶说起过,小婆当年怀着孩子,已经六七个月了。阿品叫她舂米,结果流产了。为这事,鼻公打阿品,说她是故意让自己绝后。打完了,鼻公就一个人蹲在阶沿上嚎哭。
小婆就喜欢我们这帮调皮鬼,看着我们闹,看着我们哭笑。一年大多的时间,小婆是在田野里度过的。鸟雀们见了她就一哄遁逃,小婆穿着破旧的衣服,束着作裙,头上顶一个褪了色的首巾。鸟雀们都认得她。鸟雀们怕她,倒不是这身装束,而是她喉咙里发出的声音,她赶鸟的声音,有些沙哑,仿佛猛禽,比如游隼、老鹰。生产队的麦田、稻田,往往分散成了好几个片区,阿彩一个人管不过来。再叫其他人,却又缺少人手。这么多鸟雀,一个季节该糟蹋掉多少粮食呢?队长发愁。
阿彩叫鼻公按她的模样,做了好几个稻草人。把旧衣服翻出来,给稻草人穿上,再用道林纸画了阿彩口角歪斜的脸,然后插在各处稻田内。过往的人误以为是阿彩,惊奇地说:咦!刚才看到阿彩在河南面的稻田边,那些鸟雀更是搞不明白,怎么有那么多同样的老太婆?
那年生产队分红前评工计分,队长提议说:阿彩评4分一天,有一天算一天。有人不服:凭什么?队长说:凭她用稻草人看了那么多稻田,凭她从鸟嘴中夺回了许多粮食。其实,阿彩也就每工多一个工分而已,年年如此,一直到分田到户。阿彩也老了,与鼻公、阿品去了敬老院。
如今,环境好了,树林子里什么鸟都有,白头翁、乌鸫、喜鹊,更不用说麻雀了。下来就是一大群,啄食稻麦、玉米、番茄。有人用废弃模特儿插在田里,有人用捡来的红色横幅标语,拦在半空,更有人用渔网下坎。都收效甚微。
曾经的队长,却将稻草人打扮成阿彩的模样,鸟雀远遁。阿彩早已过世多年,看来鸟雀是有记性的,而且遗传。